林毅许彦最新章节更新时间 雨歇时遇见你免费阅读全文
2025-08-15 11:31:58 编辑:蝶霜飞
《雨歇时遇见你》 小说介绍
主角是林毅许彦的小说《雨歇时遇见你》是信书倾心创作的一本双男主类小说,情节引人入胜,非常推荐。主要讲的是:第二天清晨,林毅推开“闻砚斋”的木门时,檐角还挂着未干的雨珠。风一吹,水珠滴落在青石板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像谁在地上写了个未完的句点。他照例先去擦拭柜台,...
《雨歇时遇见你》 雨歇时遇见你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第二天清晨,林毅推开“闻砚斋”的木门时,檐角还挂着未干的雨珠。风一吹,水珠滴落在青石板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像谁在地上写了个未完的句点。
他照例先去擦拭柜台,布巾掠过红木表面,带出熟悉的温润触感。目光扫过门口的伞桶,昨天借给许彦的那把黑伞不在里面——倒也不算意外,雨天借伞的客人,十有八九不会真的回头还。林毅弯了弯唇角,把这茬事抛在脑后,转身去整理书架最下层的散页。
这些散页多是从破损的古籍里拆出来的,纸页脆得像枯叶,稍一用力就可能碎裂。祖父在世时总说,“字是活的,得让它们有地方安身”,所以林毅总想着慢慢把这些散页归类、修补,哪怕最终只能凑出半本残卷。
阳光爬上窗台时,店里的檀香刚燃到一半。木门被轻轻推开,风铃发出一串清脆的响。林毅抬头,看见许彦站在门口,手里正提着那把黑色的旧伞。
他今天换了件浅灰色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线条利落的手腕。头发是干的,额前的碎发梳理得整齐,少了昨天被雨水打湿的狼狈,整个人显得更清隽些,只是眉宇间那点疏离的冷意还在。
“伞还你。”许彦走进来,把伞轻轻放进桶里,伞骨碰撞发出轻微的咔嗒声。
“多谢。”林毅放下手里的活计,“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说过会还。”许彦的语气很平淡,目光却已经越过他,落在身后的书架上,“不介意我再看看?”
“随意。”林毅做了个手势。
许彦没再说话,沿着书架慢慢走。他看得很认真,手指偶尔会在书脊上轻轻点一下,像是在辨认那些模糊的书名。阳光透过窗玻璃,在他脚下投出长长的影子,随着他的移动缓缓拉长、缩短,像在地上写着无声的注解。
林毅重新坐回柜台后,假装整理账目,眼角的余光却总忍不住跟着那人的身影。许彦停在放拓本的那排书架前,指尖在一本《熹平石经》的残拓上停了停,又轻轻移开,动作里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克制。
“你好像对拓本格外在意。”林毅忍不住开口。
许彦转过身,阳光恰好落在他脸上,让他眼底的墨色浅了些。“我父亲是拓片师傅。”他顿了顿,声音放轻了些,“小时候总看他蹲在石碑前,一待就是一整天。”
林毅愣了愣。这倒是没料到。
“后来呢?”他问。
“他走得早。”许彦的目光移向窗外,落在对街客栈的灰瓦上,“留下一箱子拓片,还有把用旧的鬃刷。”
空气静了几秒,檀香的味道漫过来,柔和了些许沉郁的气氛。林毅想起祖父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守着这些书,就像守着我”,忽然有点懂许彦刚才看拓本的眼神——那里面藏着的,或许不只是对古物的敬畏,还有些更私人的、与记忆有关的东西。
“你昨天说,在修石窟经文?”林毅换了个话题。
“嗯。”许彦转回头,“城西的千佛崖,有几处唐代的经文被风化得厉害,我来做修复方案。”
千佛崖林毅知道,离老街不远,是座快被人遗忘的石窟。小时候祖父带他去过,记得崖壁上的佛像多已残缺,经文更是模糊得像一团墨渍。
“很难吧?”他问。
“嗯。”许彦点头,语气里听不出太多情绪,“石头比纸脆,风蚀的痕迹是不可逆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稳住现在的样子,别让它们碎得更快。”
他说话时,指尖无意识地在身侧蜷了蜷,像是在模拟修复时的动作。林毅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和他正在修复的那些石刻有点像——表面看着坚硬、冷静,内里却藏着细密的纹路,得凑近了才能看清。
临近中午时,许彦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线装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走到柜台前:“这本能借看吗?”
书皮已经泛黄发脆,边角磨损得厉害,但装订还算整齐。林毅点头:“可以,不过别碰水。”
许彦找了张靠窗的椅子坐下,翻开书页。阳光落在他摊开的书上,也落在他微垂的眼睫上,投下一小片浅影。他看得很专注,偶尔会用指腹轻轻摩挲某行字,嘴唇动了动,像是在无声地念诵。
林毅没再打扰他,自己煮了壶茶,慢慢喝着。茶香混着檀香,在空气里漫成一片温和的雾。店里很安静,只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和窗外偶尔掠过的鸟鸣,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长到足够让每一粒尘埃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许彦离开时,把书放回原位,书脊对齐得整整齐齐,比林毅自己摆的还要端正。“谢了。”他说,“明天我还能来吗?”
林毅正在收拾茶具,闻言抬了抬眼:“店里的门一直开着。”
许彦的嘴角似乎极轻微地扬了一下,快得像错觉。“那我明天带些工具来,”他说,“你这里有需要修补的旧书吗?或许我能帮上忙。”
林毅愣了一下。他确实有几本棘手的残卷,纸页脆得像饼干,自己不敢轻易下手。“会不会太麻烦你?”
“不麻烦。”许彦摇头,“我正好想看看你祖父的修复手法。”
夕阳斜照进店里时,林毅站在书架前,抽出那本被许彦翻过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他轻轻翻开,在某一页的空白处,发现了一个极淡的指痕——不是污渍,更像是指尖反复摩挲留下的温度印记,浅得像一片云的影子。
他忽然想起许彦说父亲留下的那把鬃刷,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许彦果然带着个黑色的帆布包来了。包里装着修复古籍的工具:竹制的镊子、极薄的桑皮纸、装着糨糊的小瓷碗,还有一把磨得发亮的牛角刮刀。
“先从哪本开始?”他把工具在桌上摆开,动作有条不紊。
林毅取来那本最棘手的《论语》残卷。书是清代的刻本,纸页已经变成深褐色,好几处都粘在了一起,稍一用力就可能撕裂。
许彦戴上白手套,拿起镊子,指尖稳得像磐石。他没有立刻动手,而是先对着光仔细看了看纸页的纹理,又用指尖轻轻捻了捻边缘的碎纸。“是竹纸,”他低声说,“受潮后粘连的,得用温水慢慢润开。”
林毅端来温水和干净的棉片。看着许彦用棉片蘸了水,极轻柔地敷在粘连处,动作轻得像在给蝴蝶展翅。阳光透过他的指缝落在纸页上,那些蜷缩的文字仿佛在光里舒展了些。
“祖父以前用米汤做糨糊。”林毅忽然说,“他说比化学胶水更养纸。”
许彦抬眼看他,眸子里带着点笑意:“我父亲也这样。他说‘纸有灵性,得用粮食喂着’。”
两人对视一眼,都没再说话,却像有什么东西在空气里悄悄融了。檀香的味道,旧书的味道,还有许彦身上淡淡的皂角香,混在一起,酿成一种让人安心的气息。
那天下午,他们只拆开了两页残卷。许彦离开时,夕阳正把天空染成暖红色,他收拾工具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回味什么。
“明天……”他开口,又顿了顿,“我还来?”
“嗯。”林毅点头,看着他走出店门,浅灰色的衬衫在夕阳里泛着柔和的光。
木门关上,风铃又响了。林毅走到柜台前,看着许彦留下的那把牛角刮刀,刀身光滑,映出窗外渐暗的天色。他忽然觉得,这满屋子的旧书和拓本,似乎比以前热闹了些。
就像一颗投入静湖的石子,许彦的出现,在他按部就班的日子里,漾开了一圈圈细微的涟漪。
最新推荐
 弹幕说他悔疯了,可我再也不信了:后续侠名-著
弹幕说他悔疯了,可我再也不信了:后续侠名-著 死后第五年,妻子终于回心转意了:后续无名氏-著
死后第五年,妻子终于回心转意了:后续无名氏-著 绯色烬余温:绯罗萧彻无名氏-著
绯色烬余温:绯罗萧彻无名氏-著 海未眠时溺旧梦侠名-著
海未眠时溺旧梦侠名-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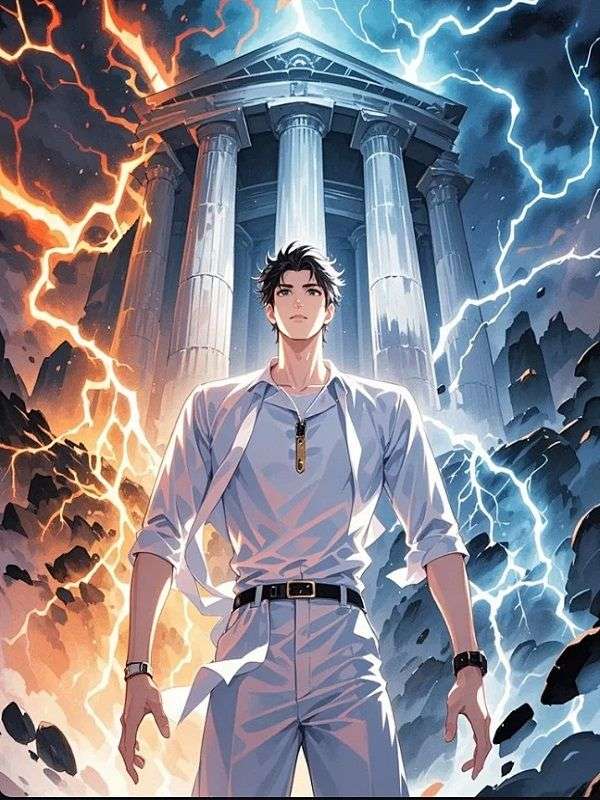 登山遇暴雨,男网红非要拍照打卡恶毒小姨-著
登山遇暴雨,男网红非要拍照打卡恶毒小姨-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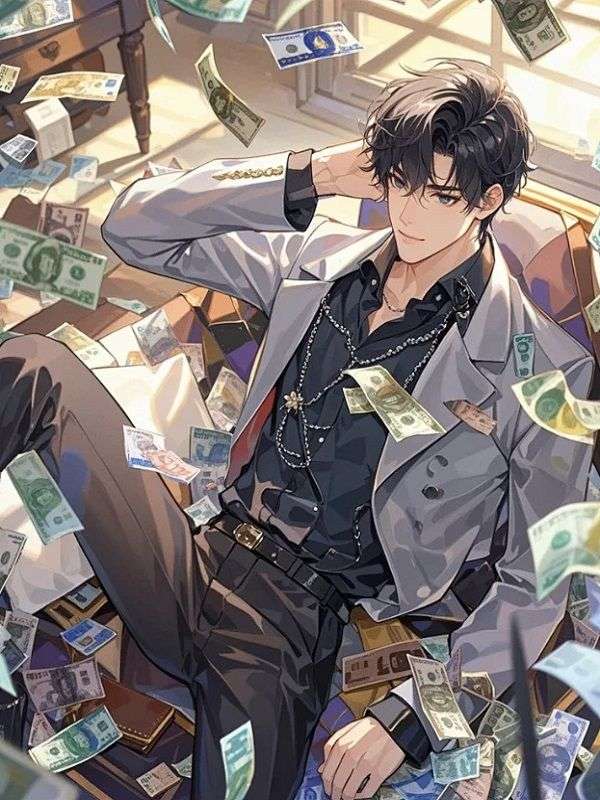 女友和竹马拍情侣视频,让我当恶毒男配且存-著
女友和竹马拍情侣视频,让我当恶毒男配且存-著
编辑推荐
 妻子逼儿子给富豪下跪后,我身份瞒不住了作者:扶正类型:总裁豪门
妻子逼儿子给富豪下跪后,我身份瞒不住了作者:扶正类型:总裁豪门 褚烟慕宸泽作者:无名氏类型:玄幻修仙
褚烟慕宸泽作者:无名氏类型:玄幻修仙 安昭棠沈泊希作者:青衫客类型:仙侠言情
安昭棠沈泊希作者:青衫客类型:仙侠言情 林北屿南梦琪作者:大神类型:现代言情
林北屿南梦琪作者:大神类型:现代言情 周介然姜书瑶作者:侠名类型:古代言情
周介然姜书瑶作者:侠名类型:古代言情
最新小说
 闭关千年回宗后,发现重孙女换了人作者:侠名类型:玄幻修仙
闭关千年回宗后,发现重孙女换了人作者:侠名类型:玄幻修仙 婚礼前夜我被绑架,主谋竟是我未婚夫作者:一千零点类型:现代言情
婚礼前夜我被绑架,主谋竟是我未婚夫作者:一千零点类型:现代言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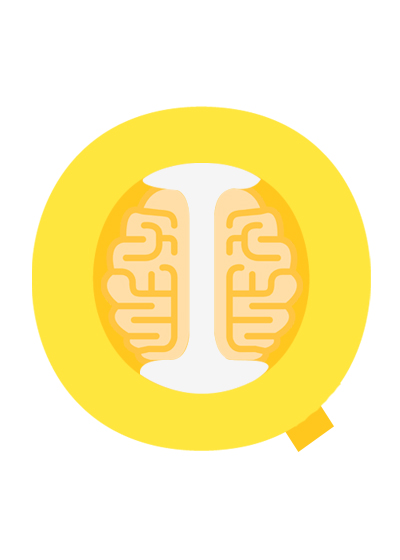 赶尸被阻后,活爷爷求我救他全家作者:英俊类型:悬疑推理
赶尸被阻后,活爷爷求我救他全家作者:英俊类型:悬疑推理 我月薪三万,却没资格心疼自己作者:一只大灰狼类型:现代都市
我月薪三万,却没资格心疼自己作者:一只大灰狼类型:现代都市 女儿被当众凌辱,全球首富的我大杀四方作者:九分裤类型:总裁豪门
女儿被当众凌辱,全球首富的我大杀四方作者:九分裤类型:总裁豪门
最新文章
周项白傅清莹宋浩林叫什么小说 死后第五年,妻子终于回心转意了:后续免费阅读小说周项白傅清莹宋浩林小说免费阅读全文 死后第五年,妻子终于回心转意了:后续小说周项白傅清莹宋浩林免费阅读周项白傅清莹宋浩林小说 死后第五年,妻子终于回心转意了:后续周项白傅清莹宋浩林全文周项白傅清莹宋浩林的小说叫什么 死后第五年,妻子终于回心转意了:后续小说周项白傅清莹宋浩林免费阅读周项白傅清莹宋浩林结局 死后第五年,妻子终于回心转意了:后续最新章节免费阅读萧临绯罗白灵兮萧彻小说结局 绯色烬余温:绯罗萧彻电子书萧临绯罗白灵兮萧彻最新章节内容 绯色烬余温:绯罗萧彻免费阅读小说萧临绯罗白灵兮萧彻和谁在一起了 绯色烬余温:绯罗萧彻小说萧临绯罗白灵兮萧彻免费阅读全文萧临绯罗白灵兮萧彻最新章节更新 绯色烬余温:绯罗萧彻全文免费阅读萧临绯罗白灵兮萧彻小说 绯色烬余温:绯罗萧彻原著在线阅读
 雨歇时遇见你
雨歇时遇见你